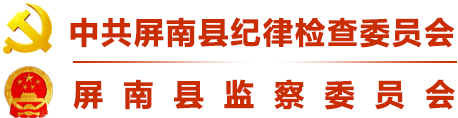要闻
龙潭:机制创新推动古村振兴

走进福建省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远处青山如黛,一湾溪水穿村而过,装饰一新的古宅矗立两岸,孕育着画室、咖啡馆、音乐厅、书屋、艺术工作室等众多“创客空间”。拿着画笔的农民,直播分享的创客,古朴的四平戏唱腔混合着电子吉他声……传统与现代在群山之间共生共荣,仿佛走入世外桃源一般。
机制活则全盘活,机制新则治理兴。通过“四为四创”,短短三年,龙潭“从古董村跨入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龙潭通过激活乡村地理价值和每个人的个体价值,革新传统生产场景、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长期研究乡村振兴的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陈建平认为,“龙潭模式”对于网络时代的偏远山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老宅为重点,创新流转机制
“村子里20年没动过一块木头,逢年过节杀头猪,本村加上周边村子都卖不动。”谈及往事,龙潭村党支部书记陈孝镇仍不禁摇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量村民外出打拼或举家外迁,原本1400人的村子只剩下100多人留守,120多栋土木结构的明清建筑日渐衰败。
为了保护古村落,从2013年开始,屏南县每年都从财政资金中拨专款维护,但是几年下来,单纯的保护工作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于是,我们开始转换思路,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将物化保护调整为活化利用。”屏南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农村人向往城市的繁华,城里人也憧憬田园的闲适,以现代理念修缮、开放“人去楼空”的乡村古宅,既能承载城市人的“乡愁”,也能让古村重新焕发生机。
一座看似破败的老宅,背后可能有几十个产权人。“占着几十分之一没有任何价值,只有收拢起来、流转出去,才能为村里发展蓄力。”曾经长期在外经商的陈孝镇眼界很宽,他说,历次农村变革,理顺村集体与村民的经济关系都是关键一环,龙潭的变革就从流转老宅开始。
龙潭人清晰记得,2017年秋天,溪水边的柿子树再次火红如丹时,村里开始迎来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先是村委会从村民手中流转旧民居,然后专家带着外地来的年轻人到村内看老宅,通过村委会将中意的老宅长期租用,并开始装修。
“以村委会为中介,出租方和承租方不发生直接关系,有效避免哄抬租金、权益纠纷等无序现象。”陈孝镇算了笔账,一方面,老宅认租15年,每年每平方米租金3元,承租方负担小;另一方面,承租方出资修缮老宅,到期后出租方无偿收回,“破木屋”变成了“黄金屋”,得到实惠。而且,老宅修缮使用本地工匠、木料,村民在家门口能做工挣钱,流转老宅的阻力也就小了。
老宅修缮充分考虑现代审美和工作、生活对空间的现代性需求,以前窄小的房间被打通,增加了现代化的卫生间,逼仄的窗户不再隐藏在宅院深处,而是大胆地在墙壁上开合,引进阳光和清风,也将古村的美景引入室内。
雨廊、河道治理、管网下地、污水处理系统等村内环境提升工程同步开展,修饰一新的村落既不失古韵,又美丽宜居。加上宁德市首个5G基站、通村公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落成,龙潭洒扫庭除,张开臂膀,笑迎八方来客。
以“高人”为牵引,创新引人机制
尽管村子扮“靓”了,但相较其他地方,从龙潭去趟县城都得沿着蜿蜒的山路开上1个小时的车,并无优势。为什么年轻创客愿意走进去、留下来?很多人的答案指向林正碌。
2015年4月,林正碌来到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教农民绘画,屏南县委、县政府为了提升成效扩大影响,同年10月在双溪镇创办了安泰艺术城提供公益艺术教学,渐渐将之发展成国内知名的公益油画教学点,每年吸引超过万名画友造访。他倡导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独特主张,着重让人发现内心的精彩,在互联网上引起许多文艺青年的共鸣。
但林正碌并不想成为“网红”。在来屏南之前,他曾经走过全国二十多个地方,试图通过文创产业让落后乡村实现就地现代化。因为公益教学的成功,他获得了屏南县政府的信任,成为官宣的“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指挥部总策划 ”,其艺术乡建理想最终得以落地龙潭。
“县领导挂钩联系,采取一人一事一议,并且在乡村建设治理中赋予我们足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林正碌说,这些更加坚定了他的选择。
林正碌的画友中,有不少人因为喜爱乡间生活的慢节奏,从双溪来到龙潭。他们每个人都辐射着身边一个同样富有创造力的群体,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个闽东北山坳深处的乡村。“这里不仅自然、人文环境好,认租、修缮老宅还有资金扶持,创业环境也好,大家愿意来。”来自江西的80后曾伟说,他与一起从老家过来的伙伴们在龙潭定了5栋房子。
曾经有投资客带着大把资金来找林正碌,让他帮着寻租一处房子,现在用来度假,以后用来养老。林正碌问都没问对方给的价码就一口拒绝了,“我们希望在龙潭建设一个拥有新的生活方式和创业方式的生机勃勃的村庄,一个有情怀、有活力的乡村家园,而不是一个景区、一个景点,甚至是一个退休养老的康养地。”林正碌说,引进创客时,不管是他们的年龄、职业以及未来的创业计划,都有严格的筛选标准,不能只是为了享受龙潭的自然山水和恬淡生活,更要做振兴乡村的践行者和推动人。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主导下,三年来,龙潭的住民数量暴增5倍至600多人。创客中有画家、诗人、音乐人、电影人、媒体人,多数还是喜爱龙潭山水、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
以创意为驱动,创新生产机制
取出一只废旧轮胎,清洗干净,染上金黄颜料,镶上圆镜,旧物被赋予新的生命……这个过程,被制作成短视频,上传至抖音。这是黄旭丹在龙潭村的日常,她的抖音号“演丹”拥有15万粉丝。除了运营抖音号,黄旭丹还是画家、龙潭小学支教老师,同时和丈夫曾伟共同经营“随喜”书屋。
和黄旭丹一样,年轻人来到龙潭,并不是成为“新农民”。网络打破了空间壁垒,他们能够以古村为“幕布”,直播分享李子柒式的田园生活,吸引更多爱好山水的人来到龙潭,走进他们开设的民宿、咖啡厅、音乐厅、写作营、画室,体验诗意的栖居。
创客们依托于互联网时代下的“粉丝经济”,辐射范围毕竟有限。而主流媒体曝光,则让龙潭的知名度呈几何级增长。2018年央视《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直播节目连线龙潭,2019年元旦,龙潭村入选国家新年升旗仪式的两个村庄之一。“央媒报道离不开龙潭自身的改变,也与挂钩联系单位的助力有关。”陈孝镇介绍,2017年底,夏兴勇从省广播影视集团来到龙潭,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龙潭也“近水楼台”获得媒体资源倾斜。
央媒关注让龙潭迎来大批游客,配套的餐饮、民宿等行业成为许多村民的选择。2019年5月,80后陈子藏带着全家老小返回了离开22年之久的故乡龙潭,在政府支持下将家中临街的两层老屋改造成餐馆,主打农家特色菜。短短半年时间便挣了七八万元,远高于在外面打工的收入。
在创客与村民的交往中,新经济业态也在悄然生长。创客为当地酿的黄酒添上包装,通过线上销售,将土产变成紧俏的商品。村民则在家门口摆上桃子、笋干、蔬菜,旁边放着收款码和电子秤,游客自行挑选、称重、付款,玩起了“无人超市”。今年五十多岁的村民谢秀凤,之前从未碰过画笔,自从学画之后便爱上了绘画,并将自家改造成了特色民宿,以画会友。
流量池越来越大,创意有了更多施展的空间。打造研学基地、开设文创集市、举办开酒节……定居龙潭的人们不拘于一业,不断探索新的可能。人才叠加乡村资金、资产、资源,生产活力竞相迸发。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让人在乡村创造不低于城市的价值,才能留住人。”陈孝镇说,在文创之外,流转闲置耕地,发展特色农业,叠加不同业态,龙潭很早就在规划未来。
以服务为导向,创新治理机制
龙潭发展起来之后,每年都有许多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前来“取经”。“大家都很重视乡村振兴,但落地是一草一木的事。”陈孝镇强调,精细化的服务是龙潭发展的基石。
早在文创项目启动之初,屏南县便成立了传统村落文创产业项目指挥部,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县、乡、村三级力量齐抓共管、上下联动,遇到问题总能及时得到反馈、处置。
为减少项目审批流程,规范项目建设管理,屏南县出台试行村级小额工程招投标管理、村账乡管、“工料法”等一批接地气的措施文件,鼓励先行先试。“村里代为购买材料、组织施工,林正碌老师在设计上予以指导,不仅省心、省时、省钱,装修风格也很时尚。”“檀舍”主人演真说,如果自己请人打造,仅装修就得上百万元。
考虑到外来创客与本地村民相处的问题,在村落改造前,龙潭便将一些村民送到双溪学习油画创作,对村民进行艺术“扫盲”。在学会画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学会与外来人的相处与沟通,让创客到龙潭实现“软着陆”。
在村一级,陈孝镇、夏兴勇把自己定位为服务者。帮助创客换灯泡、修电闸、疏通下水管道,在一件件小事中,积累起创客对龙潭的信任和依赖。2018年10月23日,在村委会协调下,龙潭村首批10位创客拿到了居住证,可以享受当地居民教育、医疗、私家车上牌等待遇,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创客们大都是网络“原住民”,为此村里专门组建由创客、村民及在外乡贤共同参与的“文明龙潭”微信群,日常问题线上反映,由龙潭村党支部、村委会提出初步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形成方案,共同执行。
“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夏兴勇说,城里人住进来,让龙潭更像新型乡村社区,“在这里,每个人都有精神输出,人与人之间又有互动”。为适应治理需要,村里建设了“龙潭乡村党校”,着力挖掘乡土人才资源,培育社区“管家”。
找到古村活化的可行性路径,培植普适性生长模式,龙潭既承担着开拓者的角色,又承担着试验种苗的意义。“龙潭村基础条件并不突出,这样的村庄做出了成绩,那就更具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屏南县县长柳岳说,龙潭的发展模式已经输出到周边的四坪村、三峰村、墘头村。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新的“龙潭片区”。
入夜,溪水潺潺,古村的呼吸平缓而惬意,散发着恬静怡人的气息,龙潭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